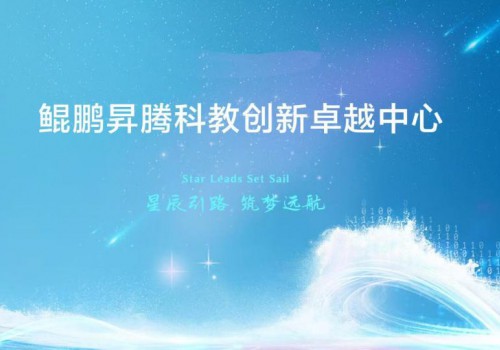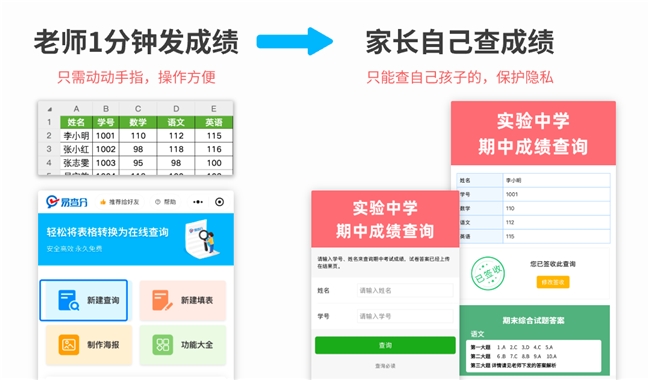赵占豪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中原大地创办了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所女子大学,先后吸收万余名二野的妇女干部、家属集中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学习生活。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对于保障二野作战的顺利进行,以及新中国妇女干部的培养和革命后代的培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我国妇女解放斗争史和我军教育史上写下了靓丽的一页。
“三个需要”催生女子大学
女子大学在二野创办,而不是在其他野战军,并非全是历史的偶然。
1948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和部队妇女、家属代表会议,这是党中央针对当时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专门召开的两个重要会议。会议要求各解放区及全军各部队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和新中国建设需要,积极培训妇女干部,促进妇女解放。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在部队妇女、家属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妇女、家属、儿童是不许可也不可能随野战军行军的。考虑到野战军的流动性、今后战争发展的形势,必须决定:除个别妇女干部宜在前线机关工作外,所有部队家属、妇女和儿童均需留在后方……适当的安置办法,就是组织起来,成立妇女学校(或工读学校)进行工作、生产、学习;把小孩集中起来,成立托儿所、幼稚园、小学进行集体抚育。”
对二野(前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来说,安置妇女家属问题的矛盾尤为突出。二野所在的晋冀鲁豫是人民军队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因为创建较早,部队家属以及根据地各级政权的妇女干部相对较多。同时,和其他野战军相比,二野在解放战争中肩负的机动作战任务又特别重。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二野始终处于大兵团远离根据地流动作战的严峻环境中。流动作战要求必须轻装前进,留在后方的妇女干部以及家属子女无疑成为二野部队的后顾之忧。因而,早在1946年到1948年间,二野各纵队(或旅)就先后在后方创办了妇女学校(职业学校或家属学校),安置留守的妇女儿童。总政创办妇女学校的决定,正是对二野经验的总结推广。中央“两个妇女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二野把原有的妇校集中起来,在山西晋城建立了南线妇女总校,全校人员约8000余人,这就是二野女子大学的前身。
女子大学的成功创办,离不开二野首长特别是司令员刘伯承的重视和推动。刘伯承一贯重视教育工作,并且具有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早在1948年9月,为解除后顾之忧、稳定前线将士,他即提出了创办女子大学的构想,中央“两个妇女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强化了办学的战略需求。淮海战役结束后,南线妇女总校的近千户随军家属带着孩子,从华北来到中原与家人团聚。如何妥善安置好这批人员,成为部队渡江作战准备中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1949年3月,刘伯承亲自主持首长办公会,“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新中国培养妇女干部的需要,为妇女彻底解放的需要”,决定在南线妇女总校的基础上成立二野女子大学,并亲自兼任二野女大的校长和政委。
二野女大创办时期,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刘伯承在戎马倥偬、运筹帷幄之余,经常过问女大的诸多重大问题,强调指出:“一定要把女大办好”,“要选拔好学校的领导干部”,“要物色好教师”,“女大要像‘红大‘抗大一样,要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并且亲自审定女大的教学计划,提出学习的目的和任务。领导对女大的重视和关心,使妇女干部、家属深受鼓舞,全校官兵师生积极性高涨,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把学校办好。
应该说,和之前的南线妇女总校相比,女子大学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等方面其实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女子大学”的名称,特别是“做刘伯承司令员的学生”,在当时对渴望随亲人渡江南进的众多妇女干部和部队家属们,还是起到了有力的动员作用。
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大的创办,不仅起到了解放妇女、培养妇女干部的作用,而且成为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招,对前线浴血奋战的二野将士,发挥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的奇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女大的创办,似乎是对刘伯承 “治军必先治校”这一名言别有意味的注解。
“你们在前方打老蒋,我们在后方学本领”
1949年三四月份,二野女大正式开学。学校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的河南巩县、偃师、新郑等地区,共有9000余人。学校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主要从二野总部及各兵团抽调,一部分老师是从开封、郑州、洛阳、南京等地聘请的。女大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建制,师生员工都属军队在编人员,享受供给制待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严格按照革命化、军事化的行为规范要求官兵师生,是二野女大的重要特色。
女子大学的学员,大部分是原南线妇女总校的学员,其中有老根据地政权中地区、县、乡、村干部,也有部队的干部、卫生员、宣传员和技术人员,相当一部分是二野团以上干部的家属、子女,还有个别国民党投诚军官的家属。建校初期,女大的干部和学员都存在一些思想问题。个别干部教员觉得从一线部队来到女大,“给别人看老婆孩子”,工作不好做,没有出息;部分学员学习目的不明确,刚离开亲人感觉不习惯、不方便,有的担心前方,有的有小孩拉扯,学习不便,还有的觉得自己文化太低,学习有困难。针对这些情况,女大深入开展了学习讨论和思想教育,学员们很快端正了思想认识,树立了正确的奋斗目标,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女大的教学内容,除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文化课以外,还开设了政工、保育、卫生、财会、歌咏和医护训练班。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不同和有无孩子编成不同的队和班,因人施教。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战争形势,注重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政治课以时事政治教育为主,使学员了解革命发展形势和我党、我军的各项方针政策,继承部队光荣传统,坚定革命意志;地理课结合部队南下进军路线,打到哪里讲到哪里;算术课把我军消灭敌军的数量、缴获的各种武器装备,编入加减乘除运算题;语文课上,教学员写信,给前方爱人写,给老家写,给部队写慰问信,通过写信,学以致用,既激发了学员学习的热情,也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学员们自编了识字歌:“不识字,真可怜,爱人来信不会念,左看右看看不懂,真是急死人。识了字,放光明,《新华日报》能看懂,爱人书信不求人,心里真高兴。”学校对每门功课、每个学习阶段都要进行考试,检测学习效果,督促学员学习。学习成绩进行公布,并组织学习成果展览,对于学习好的学员给予表扬和奖励,以鼓励教学双方的积极性。
虽然当时的办学条件很差,但学员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没有教室,就以庙宇、祠堂、仓库、院坝甚至树下当课堂;黑板是用锅灰在墙上或门板上涂成的;桌凳是从老乡家里借的;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练,或者睡觉时用手指在身上划。学员们在学习上争先恐后、互教互学,中午不午休,晚上熄灯后还悄悄默读。有的当母亲的学员,晚上一手抱小孩,一手写字做作业。总校、分校都办有校报刊物,各大队、中队都办有俱乐部和墙报学习园地。学员队广泛开展“插红旗树标兵,比成绩帮后进”活动,不断掀起学习竞赛的热潮。学员们说,前方的男同志英勇作战打胜仗,我们在后方要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作为今后与他们会合时的“见面礼”。有的学员给丈夫写信说:“你们在前方打老蒋,我们在后方学本领,你们拿枪杆呀,我们拿笔杆,咱们比一比呀看一看,看谁的名字在最前面。”
通过刻苦的学习,学员的文化水平普遍有了明显提高。原来是文盲半文盲的同志,经过一年的学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小学文化程度,部分学员语文达到初中水平,能读书看报写文章,为以后工作或继续学习打下了基础。
平常,女大师生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学员们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着军服、戴军帽、扎皮带、打绑腿,定期检查军容风纪;早出操、晚点名;上课就餐都要集合站队、唱队列歌、喊口号;每周各分校要进行一次学习总结,各班要开一次班务会;集体活动时还会进行拉歌比赛;对外交往时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员之间朝夕相处,情同姊妹,亲如一家,在学习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学员常勇的丈夫上了前线,她来到学校时怀有身孕。在怀孕后期,同学们每天给她打好洗脸、洗脚水,想方设法给她做可口的饭菜。她坐月子期间,同学们都争着帮她洗衣裳、尿布,给她和孩子熬米粥、调米粉,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她非常感动,她的丈夫在前线也十分欣慰。这样的事情在女大比比皆是。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是女大的一大特色。当时,各分校都有业余文艺宣传队或文工团。总校还专门举办了文艺训练班,为分校培训文艺骨干。各学员队都建立了俱乐部,学员人人参与,各中队都有“拿手戏”。学员们创作的“学习歌”“劳动歌”“立功歌”等数十首歌曲人人会唱,激励着大家比学赶帮、争当模范。业余文工团排演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节目在校内外演出后,引起了轰动。
女大学员革命军人的风采,给解放区带去了一股新时尚,使驻地乡亲们耳目一新。乡亲们感慨地说:“女大的学员多是解放军的干部家属,但她们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军的官太太。”
秋季“大生产”
从1949年8月开始,女大在喜迎新中国诞生的同时,也高兴地迎来了秋季“大生产”。这可不是收割田里的庄稼,而是女大这个大家庭添丁进口。由于年初部队休整期间的家属大探亲,许多学员同时怀孕,同时“害喜”,同时大腹便便,同时临产。每个分校都有二三百名孕妇,加上总校,共有千余人待产。在当时,如何保证这千余个革命后代平安出世,成为女大那一阶段的重大任务,总校及各分校为此都作了紧急动员、全面布置。
组建女大时,二野从各兵团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总校和4个分校都设有卫生领导机构,总校设有医院,分校设休养所,大队设卫生所。为提高妇产科技术水平,总校医院举办了妇产科训练班,为各分校培训接生人员。同时还规定,孕妇产期为50天,住进休养所后吃中灶,产后吃小灶,切实保证产期前后的营养。据四分校保育人员回忆:从7月初开始,卫生所的同志就忙得顾不上吃饭。对产妇逐个进行产前检查,凡有难产迹象的,就送总校医院处理,先后送走20多个。接生员不够,又从驻地找来几十个旧式产婆,加以训练,严格规定消毒、操作过程,然后分派到6个大队,每队八九人。8月起,第一批婴儿开始降生,9月达到高潮,有时一天出生10余个孩子。卫生所的领导轮流去各队检查,看望产妇和新生婴儿,按规定发给母子营养钱物。这股生产热潮一直持续到10月份。经过辛勤努力,女大顺利完成了这空前独特的秋季“大生产”任务,千余名小宝宝平安降生,为女大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喜庆。当时各分校都流传一个笑话:“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生了一个营,大人孩子个个健壮。”
由于战争环境及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大生产”在给女大带来欢笑的同时也不免伴着泪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女大四分校有一位名叫龚淑贞的学员,1946年由河北农村投身革命,在根据地被服厂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49年初,龚淑贞与十五军一位同样来自河北的赵姓干部结婚,就在新婚蜜月中,爱人奉命上了前线,她则被安排来到女大进行学习。和丈夫在一起的短暂幸福生活,给她留下了爱情的结晶。当这位年轻的妻子把将要做母亲的兴奋心情写信告诉前方的丈夫时,丈夫却还没来得及给她回一封信,给孩子起个名字,就在渡江战役中光荣牺牲。噩耗传来,体弱多病的龚淑贞悲痛万分。当孩子即将出世时,她由于难产,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保大人或保孩子只能做出一个选择,这位年轻的母亲坚决要求医护人员一定要保孩子,给丈夫家留下革命的后代。为了把不足月的孩子生下来,龚淑贞痛苦地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昏迷前还在哀求:胜利后一定要把孩子送给河北赵家。随后,龚淑贞便一直陷入昏迷,医护人员研究后,决定用手术钳把孩子拖出来,随后又奋力抢救大人,但龚淑贞最终没能听到孩子的一声啼哭,便永远诀别了人世,只留下了一个没有名字的烈士遗孤——毛孩。
母亲走了,刚刚出世的毛孩也危在旦夕,不会啼哭、心脏跳动微弱,医护人员用3个热水袋保暖才把毛孩抢救了过来。四分校从学校领导到每个学员都十分关心毛孩,其他产妇每天都把奶水节省下来给毛孩吃,有的还送来了小衣服。毛孩满月后,学校又给他找一个专职的“母亲”照顾他。最终,在女大这个娘子军中,在百家母亲们的悉心照料下,毛孩一天天健康成长,后来得到了妥善安置。
和教学工作一样,保育工作也是二野女大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且是独具特色的一项内容。女大各级领导在中央军委、刘邓首长关于“儿童是革命的新生后代,是未来的主人,是党的一批财产”,“我们办学校就是培养妇女干部、培养革命后代,也就是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的思想指导下,把培养教育革命后代工作纳入女大工作的总计划和日常工作内,自始至终紧抓不松懈。
女大总校和各分校都专门设有保育工作领导管理机构,并相应开办了育才小学、托儿所、幼稚园。到1949年11月,全校共办起10个幼稚园、14个托儿所,共有儿童622名,保育员200多名。此外,还办了4个育才小学,约有500余名学生。为做好儿童的教育工作,女大专门聘请了老师,并组织了保育人员训练班。在战争时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女大仍力求优先保障好妇女儿童的后勤供应和卫生保健。女大学员的各项生活供给标准按野战军待遇,儿童灶有白面和肉,还有专门的保育费,女大学员中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一个孩子是中农,两个孩子是富农,三个孩子是地主”,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野及各兵团首长也非常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与生活,把前方缴获的战利品源源不断地送来,花花绿绿的洋布给孩子们做衣服,大桶的罐头、奶粉、饼干等给孩子们改善生活,并派工作人员和记者来了解幼稚园情况,给孩子们照相,制成幻灯片到前方放映,使女大全体师生备受鼓舞。
搞好军民团结,支援地方建设
女大的师生们在加强学习、带好小孩的同时,还主动参加生产和地方工作,为支援前线作战和密切军民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全校师生发挥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自己的双手参加生产劳动建设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他们通过种菜、养猪、生豆芽、磨豆腐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还力所能及地办些小工厂为社会创造财富,加班加点做军衣、军被。这些措施在节约自身开支的同时,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在课余,女大师生积极向驻地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各个宣传队的女学员自编自演,采取街头报剧、秧歌舞剧、打花鼓等形式,灵活地进行宣传,收到良好的效果。生活中,学员们热情地帮助当地群众挑水、扫院,农忙季节还主动帮助群众春耕秋收。同时,女大师生还组织民运工作队,参加地方的土改工作和反匪霸斗争,为当地新生政权的建设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新郑县志》记载:1949年3 月,四分校学员宋光华带领该校民运工作队130多人,参加新郑县的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效,宋光华等十多位学员因此被留在新郑县参加地方政府工作。
二野解放大西南后,于1950年2月电令女大:抓紧时间总结一年来的教育工作,对全校干部、教师、学员进行鉴定,然后前往西南与总部和各兵团会合。1950年3月,总校和各分校分别从河南驻地出发,向南开进。一路上,女大师生不仅要战胜各种自然困难,而且还要同土匪和残敌作斗争。三分校入川途经鄂川交界地区,流落那里的国民党溃兵时常放冷枪冷炮,搞破坏活动,分校官兵组织起来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四分校途经广西柳州时,参加当地的清查反革命运动,协助当地军管会抓获16个特务;在云南、贵州境内,还歼灭小股土匪,打死土匪多人,自己无一伤亡。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各分校胜利到达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完成了归建任务。
1950年4月,西南军区政治部发出了《对军队中妇女儿童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二野女子大学的工作,指出“这一大批妇女干部是可用的力量”,要求“将她们作妥善安排,对她们的工作等级与待遇应同男干部一样对待”。二野女大的官兵、师生,纷纷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女大由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野女大的学员后来有一半以上担任了各级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有的成为财会、文秘、卫生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女子大学育才学校和幼稚园的近2000名少年儿童,解放后也成了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有的还成了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编辑:徐 嘉)
此文由 中国教育导报-高中编辑,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中国教育导报 > 高中 » 特殊时期的二野女子大学